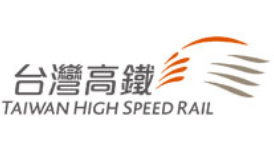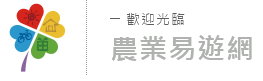(地政士林瑞明專欄)在現代社會,隨著財產型態的多元化與家庭結構的轉變,遺產繼承的安排愈發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許多人希望藉由立遺囑來明確表達自己對財產分配的意願,以避免親屬間的糾紛。然而,法律制度設計並非僅以「個人意思自治」為唯一準則,而是兼顧「被繼承人生前自主決定」與「繼承人最低生活保障」之間的平衡。於是,「如何擬定遺囑」與「能否排除特留分」便成為必須正視的問題。
《遺囑的五種法定方式》
依《民法》1189條至1195條規定,我國承認五種有效遺囑形式:
1. 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全文、日期與簽名。
2. 公證遺囑:由遺囑人口述,經公證人與兩名證人製作筆錄並宣讀確認。
3. 密封遺囑:由遺囑人簽名後封緘,再交付公證人與證人簽認。
4. 口授遺囑:在危急情況下,由遺囑人口授,經兩名以上證人筆錄。
5. 代筆遺囑:遺囑人口述,經他人代筆並有證人簽名。
這些方式之所以嚴格,乃是為防止爭議與偽造,確保遺囑真實反映遺囑人的最終意志。
《特留分制度的存在意義》
然而,遺囑自由並非毫無限制。《民法》明定所謂「特留分」制度,保障直系血親卑親屬(子女、孫子女)、父母、配偶,依法享有一定比例的最低繼承份額。其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遺囑人因情感或衝突,將至親完全排除於繼承之外,導致生活陷入困境。
換言之,即使立遺囑將財產全數留給某一人,受侵害的特留分繼承人仍可依法聲請「特留分減少請求權」,要求回復到其應有的最低保障份額。這項制度,正是法律平衡「個人意思自治」與「家庭倫理保障」的具體展現。
《遺囑能否排除特留分?》
若問:「遺囑是否可以明文排除特留分?」答案是:不能有效排除。遺囑人固然可以在內容上聲明「不讓某子女繼承」或「將全部財產贈與他人」,但該聲明並不影響特留分的法律效力。只要繼承人依法主張,法院仍會認定該部分遺囑超過特留分的安排無效。
法律依據可見於《民法》第1223條規定「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二、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四、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五、祖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因此,任何試圖藉由遺囑全面剝奪配偶或子女繼承權的做法,最終都將因特留分保障而受到限制。
另外,繼承人對遺囑內容有爭執,最後仍得經過法院判決,其過程曠日廢時,若在生前製作遺囑排除特定繼承人繼承權,依據民法第1145條:「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繼承權:…五、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
實務上,不肖子女可能長年在外對父母不聞不問,因為符合剝奪繼承權規定的有重大虐待或侮辱-必須子女有「動作」,對父母不聞不問,難以說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法院可能難以判決如遺囑人之所願,「大禹治水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古代沒有電話。大禹對父母不聞不問,難道就可以剝奪大禹的繼承權嗎?」,因此坊間有專業人士聲稱立遺囑可以排除擁有特留分繼承人之繼承權之說,千萬不可採信!
《社會觀點:保障與改革的辯證》
從制度觀之,特留分保障了基本的倫理秩序與生活安全,避免「財富傳承」淪為「懲罰工具」。然而,也有人批評,特留分制度限制了財產所有人對其財產的最終處分自由,尤其在親子關係惡劣或繼承人毫無扶養義務履行時,更顯得不公。
因此,近年社會上逐漸出現改革聲音,主張應放寬遺囑自由,或至少排除部分繼承人(例如成年子女)之特留分保障。這樣的討論,正折射出社會對「家庭責任」與「個人自主」不同價值的拉鋸。
《結語》
遺囑的擬定,是個人一生中最後的法律選擇,其形式必須符合法律規範,其內容也受到特留分制度的拘束。雖然遺囑自由看似受限,但這種限制正是法律對弱勢繼承人最低保障的體現。若社會未來要朝更高程度的遺囑自由邁進,勢必要伴隨完善的社會福利與倫理討論,否則財產自由處分與家庭責任之間的平衡將難以維繫。在此之前,任何試圖透過遺囑「排除特留分」的安排,都只能是形式上的聲明,卻難以在法律上獲得實效。(撰文者為執業三十年地政士、現任台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理事長)